抗战记忆:诗人卞之琳与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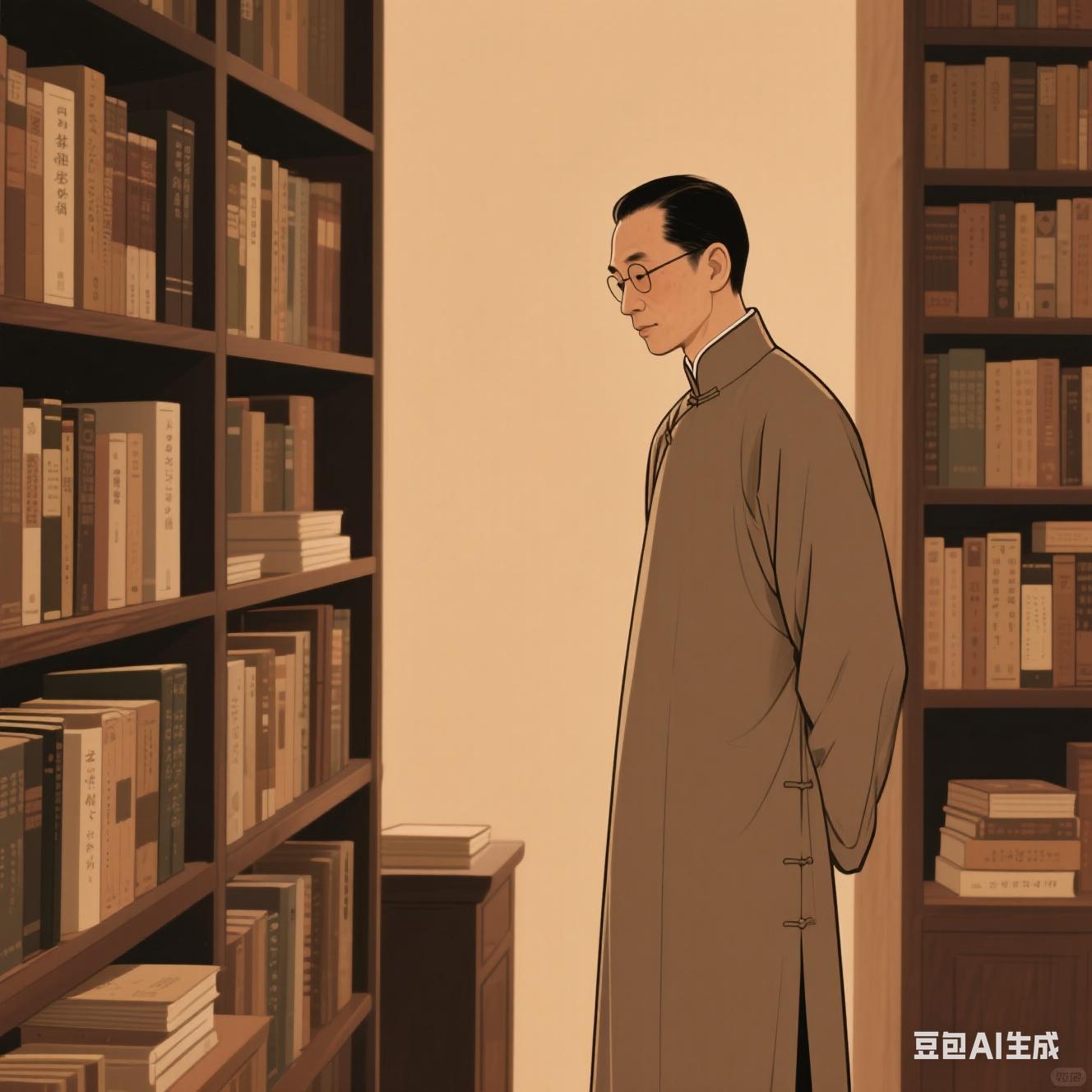
1910年12月,卞之琳出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23岁时出版第一部诗集,25岁时即以一首既有意境又有哲学意味的《断章》而蜚声诗坛。“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显然是一首象征主义新诗,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卞之琳早年受波德莱尔、魏尔伦和瓦莱里等西方自由意象派诗人的影响,时刻沉醉于对生命的沉思和对美丽事物的感悟。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和升级,诗人个体的浪漫便渐渐被一种更大的情怀所替代,激发出更强烈的情感、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具生命力的形式。
作于1934年春的长诗《春城》可被视为卞之琳诗风转变的滥觞,虽然其早期标志性意象诗《断章》还在《春城》之后完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在这一年半之后的1933年春至1934年春,中日政治军事形势由暂时的平静急转直下,日本战机几乎天天盘旋在中国人的头顶,无论是东北还是华北。中国诗人中激起了抗议的声浪。卞之琳也抛下文人远离政治的清高态度,写了一首《春城》长诗,这首诗就其长度、语气和写实性而言,与卞之琳早期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诗中以貌似俏皮实则讽刺的语调表达了对政局的沮丧和不满:“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鹞鹰……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一枚炸弹——哈哈哈哈”“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觉,幸亏瓦片儿倒还有眼睛,鸟矢儿也有眼睛,哈哈哈……今儿天气才真是好呢,看街上花树也坐了独轮车游春,春完了又可以在红纱灯下看牡丹。天上是鸽铃声——蓝天白鸽,渺无飞机,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决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
此后,随着对抗战和时局积极的深入和融入,卞之琳全面成长为一名爱国政治抒情诗诗人。
1937年7月,卞之琳27岁,抗战全面爆发。8月15日,他从浙江雁荡山辗转回到上海,9月初,离开上海经由武汉到成都。次年3月,与何其芳、方敬、朱光潜、谢文炳等创办《工作》半月刊,以“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为共同目标。这本刊物全面记录和反映了诗人们诗风的转变,就卞之琳而言,由他翻译的著名诗人纪德“左”倾时期的作品《新的粮食》在这份爱国刊物上连载,描写抗战实况的散文《地图在动》也发表了好几则。除去在言论上支持抗战和正义,诗人们还在积极筹划一项实际的支持行动。
1938年8月14日,一切准备就绪。卞之琳与沙汀夫妇、何其芳背上简单的行囊从成都出发,踏上了“朝圣”之旅。他们沿川陕公路一路北行,8月24日到达陕北宝鸡,次日改乘陇海线快车至西安,在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接待,28日搭乘办事处汽车前往延安,31日抵达延安。在延安,他们换上了延安党政机关与军队的统一着装:灰布制服。9月初,边区教育厅长、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安排他们见了毛泽东。就在等待出发去前线期间,卞之琳研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1月12日,卞之琳正式成为一名文工团成员随军出发。他们跟随朱德总司令一行,过西安、潼关、渑池,渡黄河,经山西垣曲、阳城,最终抵达襄垣附近的十八路集团军总部。1939年年初,卞之琳随即与吴伯萧翻越太行山……1939年4月至5月间,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在延安驻留了三至四个月,8月末回到四川大学复职。
卞之琳前前后后辗转在前线和延安大概一年之久,深度体验和采访,延安被他称作是“另一个世界”。卞之琳不仅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他还接触到中国内地“山山水水”的真实状况。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的敏锐,卞之琳创作了十八首政治抒情诗、好几篇短篇小说,以及数十篇战地散文和通讯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慰劳信集》,《一切劳苦者》在诗集中属于最后统冠的地位,也最能体现这趟延安之行对他的革命洗礼:啊!只偶尔想起了几只手,我就像拉起了一串长链,一只牵一只,就没有尽头,男女老少的,甚至背面多汗毛的,拿着锄头、铁锹、枪杆、针线……以至于无限。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破路与修路,拆桥与修桥,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重要,一块只是砖,拼起来才是房,虽然只几块嵌屋名与房号,不怕进几步,也许要退几步,四季旋转了,岁月才运行,身体或不能受繁叶荫护,树身充实了你们的手心,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
卞之琳诗风转变的背后其实是革命信仰及时代关注的转变。前者是形式,后者是本质,两者之间互为映照与适应。形式与本质的融合引导诗人走向更为宏阔的未来。
1939年8月末,卞之琳离开延安回到国统区的四川大学重执教鞭。同年秋天,跟随川大到达川大的峨眉山临时驻地。他在这里完成了《慰劳信集》和《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手稿,其他有些诗作已陆续发表在延安的《文艺战线》杂志。1940年年初,川大已经难以接受卞志琳的政治立场,他被解聘。卞之琳南下昆明,接受了西南联大的讲师职位。西南联大是卞之琳在抗战时期的新舞台。在这里,卞之琳找到了文学圈的朋友:《汉园集》的作者李广田,卞之琳以前的编辑同事、诗人冯至,最重要的故人是闻一多。闻一多在昆明一边教课,一边做中国古诗起源的研究,同时充当年轻一代诗人的精神导师。卞之琳到达昆明不久,延安西北之行的两个成果《慰劳信集》和《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就由明日社出版。《中国现代诗歌》编者陈世骧在美国杂志《亚洲》上重点推介《慰劳信集》,刻意突出和强调了卞之琳转变之后的新形象:“一位战时诗人,非常优秀的战时诗人!”《慰劳信集》得到了闻一多的盛赞。卞之琳最初进入诗歌的殿堂,闻一多的新诗《死水》是启蒙之一,可以说闻一多与卞之琳是亦师亦兄亦友的关系。
而彼时闻一多已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忠诚盟友的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中坚力量,民盟第一个省支部——云南省支部领导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也大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如此一种爱国与革命氛围的影响和熏陶,诗人卞之琳的灵魂又一次受到强劲的洗礼。卞之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三年加入民盟,继后不久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尔后在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毫不动摇地成了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福祉摇旗呐喊的新时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