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味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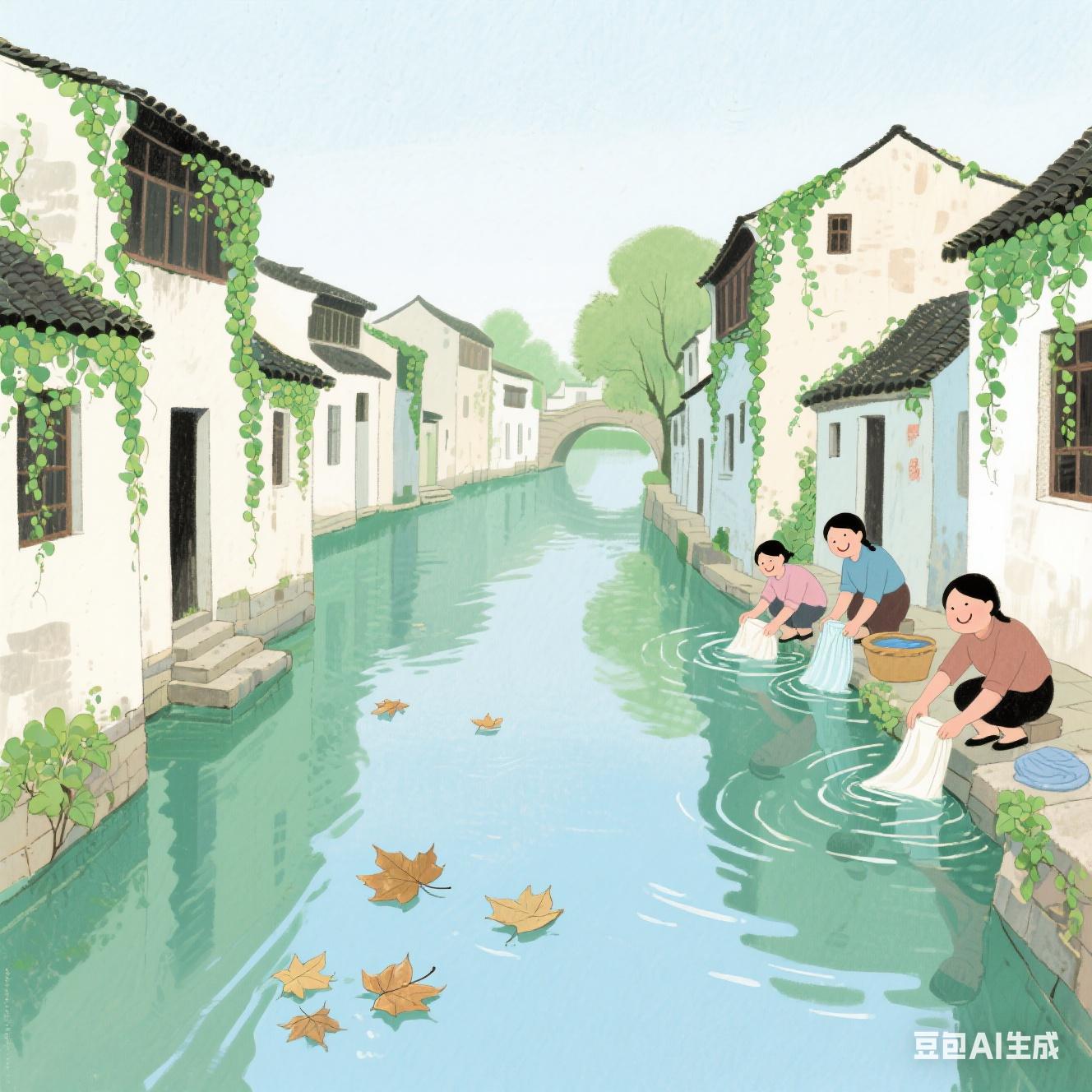
大约位于北纬32°、东经121°这个坐标点就是丰利。丰利场建置之始可追溯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丰利”之名,寓意丰饶与利益,是盐业或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丰利场最初隶属于如皋县,历经元、明、清、民国,行政区划长期稳定。直至1945年如东县设立,丰利才改隶如东县。作为一个历史重镇,丰利见证了千年变迁,虽底蕴深厚,却因近代战乱与社会动荡,相关文物史料损失严重,系统的地方志书竟告阙如。
丰利是我的出生地,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因为我而去寻找丰利?我不得而知。我似乎说得有些自信、轻狂与不自量力。对于我,丰利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丰利是盐碱地上一处活着的所在。
先人们“煮海为盐”,老辈人讲起这些时,眼睛便放出光来。他们说“黑风口”的浪头如何凶险,先人们如何与海争命,盐粒如何在灶上结晶。我听得多了,并不觉得他们夸大其词。我总以为艰苦的事情历经风雨打磨,也会显出几分光彩。
世间的变化往往是瞬间的事。海边立起了巨大的风车,白色的叶片缓缓转动,发出低沉的嗡鸣。年轻人谈论的不再是潮汐和鱼汛,而是“清洁能源”和“智能养殖”。老渔民们看着这些新奇事物,既羡慕又困惑,他们知道大海还是那个大海,但捕鱼手段、方式和往昔大相径庭。
我见过老盐工的手,粗糙如树皮,也见过年轻创业者对着图纸讨论时的神采飞扬。他们与父辈们手里的网绳织着不同的经纬,这两代人看似毫无共通之处,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息息。大海永远在那里,给了他们生计,也给了他们满脸沧桑。
好多人喜欢把自己的故乡比作港湾、摇篮、灯塔,在我看来,不免有些俗气,我更愿意把丰利比作根。丰利的根深扎在渔盐文化的沃土里。汗水与海水交融,结晶成雪白的盐粒,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丰利人。
丰利现在是怎样的面貌呢?说它是古镇,它有了新城的模样;说它是新城,骨子里仍有古镇的影子。新城的楼角与老街的飞檐相望,丰利像极了堤岸上的杉树,根伸向咸水里,枝干却拼命朝上生长。潮水来了又退,浪花碎了又生,丰利就在这进退碎生中悄悄改变着容颜。
老街上原来的青石板已经换成高低不平的条石,雨天里泛着幽光。两旁的店铺关闭多户,偶有几家还在勉强支撑。昔日,盐商们在此交易,讨价还价,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盐商们的声音消逝在光阴的风中,只剩下几个老人闲坐着,啜着浓茶,回忆“丰利场”的旧事。他们的回忆仿佛茶汤上的热气,飘忽不定,终将散去。
我离开已久,偶尔回去,总觉陌生。熟悉的街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空关的老屋。没事时,我找丰利一帮文化老人聊天,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镇上的趣闻、传说以及古往今来。文昌宫、文园、土山祠、五人墓、宋朝的井、张謇在丰利办公的场所等等,这些旧址还在。我一一看了,心想这是可以恢复的,如果重视一下,哪怕因陋就简花点小钱,就能保存下来,也好对后代讲故事了。都说“先有大圣寺,后有丰利”。丰利大圣寺花了二十年时间,在那片几近荒芜的农田上建了起来,而今像模像样了。于丰利而言,大圣寺既是香火缭绕、梵音袅袅的宗教圣地,也为小镇居民提供了充满生活气息的休闲佳所。丰利大圣寺从重建之初到颇具规模,这件需要长久坚持的事,有多少人能做到?个中之艰难困苦又有多少人能知晓?丰利这帮老人真是了不起,他们认为丰利古有十景消失了,现在担心遗存的东西也会丢失掉,那些明清朝的老屋,屋顶都起洞了,在日光里抖落岁月的尘埃,再不修缮就会倒塌。
丰利文化老人有珍爱、尊崇之心,用皱纹里的故事给老街续气。我能理解他们,他们期待丰利能成为有文化传承的地方,因为老街是丰利的根脉,承载着几代人共同的回想及眷念。
镇上、社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好多事不是想办就能办的。很多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类似情况,但目前的财力难以解决。当然,不是恢复了古镇就是发展、进步了,我只是说,镇区的面貌就像一个人穿衣服,不一定非要穿新的不可,至少要干干净净。丰利老街能不能把路铺平整?对于破烂、无价值的房屋,动员住户维修、拆除或出售,不至于有败落、颓废之感,这大概应该可以做到,也一定能做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老街修建、恢复好,更没有任何理由不把丰利这张集教育、文化、民俗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老字号”名片擦亮,这是不可推诿的历史与当代责任!
或许所有的故乡都是异乡,而真正的异乡会在某个时刻成为灵魂的故乡,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知道,有些东西比砖瓦更坚硬,是盐碱地长出的韧性,是与海共生的智慧,是刻在血脉里的印记。相信丰利的将来会愈发光鲜亮丽,但那与我记忆中的丰利怕是再难重合了。